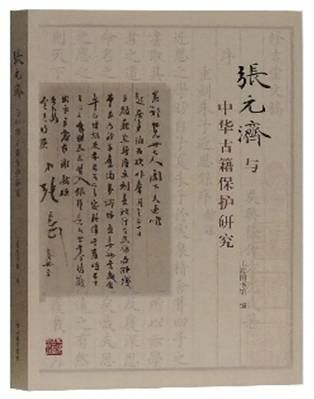
于我自己而言,无论是张元济先生还是古籍保护研究都是陌生的。只有当我打开了这本书之后,我才开始了解这位将一生都投入中国文化、出版、藏书事业的先生。从本书中收录的二十来篇关于先生以及中华古籍保护研究的论文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先生的嗜书如命。先生晚年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先生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嗜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先生的一生。
在书中文章《《百衲本二十四史:现代古籍整理的典范》中柳和城写到“张元济先生向来主张为古人“续命”,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古书印出来,流传下去;多印一部,多流传一部,也就是多续古代文化之命,多续民族文化之命。” 在张元济先生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用力最勤、费神最多的当属《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两部大书在文化上的影响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在整理《四部丛刊》时,先生已是花甲之年,但他仍然为了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专程奔赴日本访书,并且经常做笔记到深夜,每到一处都商借拍摄,带回上海影印出版。古籍的墨迹不清是常见的事情,这就需要用心将不清楚的字迹描绘清晰,这是校勘古籍的最初步骤,专业术语叫做描润。先生仍然亲历亲为,对每一册古书,做着初修、精修、复校、总校的工作。他终日伏案,每天校勘100页,直到每一页都校勘到准确无误为止。直到今天,看过先生校勘影印件的人,都叹为观止。而之后,先生又进行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这一伟大工程。他坚持从民间流传的众多版本中挑选出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其工程量十分浩大,是我们当代习惯了海量信息自动化、智能化的网民们无法想象的。顾廷龙先生曾感叹道“这么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写的,那些校勘记,那些批注,所耗费的精力工夫无法估量,这整整十年当中张元济就是每天不间断地在做这样一件工作!”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张先生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一样的是,在那个大多数知识分子走上“文化救国”道路的年代,唯有先生选择了出版,站到幕后。我们在认识那么多手拿纸笔做武器的仁人志士,为他们的清醒、为他们的犀利言语感到振奋的同时,也应该向更多先生这样的“幕后工作者”致敬!





